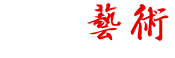石丰
艺术家 :
石丰
作品欣赏
艺术家介绍
感恩父母,感恩父爱!
文图/石丰

上世纪1981年的春天,父亲在老家当地薛录镇供销社工作。他从《陕西日报》上看到一则消息: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招生。由于我从小爱好美术,得到全家的大力支持,即是我画得越来越入门,他也不爱轻易地表扬和鼓励于我,但他依然欣喜,确是事实。

父亲决定,我们去西安赶考一趟。按报纸上的广告要求,我们做了一些准备。母亲让我穿上新衣,去照相馆照相,她专门烙了两个厚实的锅盔,让我们在路上以当干粮。
记得那天,我和父亲起得很早,老家的公鸡可能刚打四更,天还没有放亮,我们各自骑上一辆自行车,向目的地,向我从来见过、没有去过的伟大的梦里大城——西安,进发!
老家,五月的早晨,天气依然清凉,但空气非常新鲜。自行车骑在乡间的小路上有些颠簸,父亲骑车在我前面,由他给我带路。
老家距离省城70多公里,由312国道西兰公路直达省城西安。当时,这样的距离,对我来说没有多少概念,父亲说,骑自行车大约需要四个小时左右。够长,我平时最多骑过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。
我们沿西兰公路向东前行,一个多小时后,天边扯出了一缕一缕的朝霞,和公路两边翻滚的麦浪一起,染得我的心情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。
不知骑了多长时间,父亲发现我已掉队,他放慢了速度说:坚持一下,我们在前面茶摊子那里吃饭喝水,休息会儿再走。
大约骑行十多分钟,到达公路沿边的茶摊。卖茶的老汉和我爷一样,都是纯朴矍铄的关中老汉,他戴着黄铜架子的圆眼镜,给我和父亲热心地端板凳,倒茶水。八十年代的路边茶水,由两种玻璃杯盛装,小杯售价一分,大杯二分钱。
我不知道父亲是否饥饿,我反正饿了。我从随带的帆布挎包中,取出母亲带给我们的锅盔,就着茶水,咬着锅盔。我由于吃得着急,或者生猛,不小心被锅盔噎了一下,憋得我非常难受,父亲马上提醒我:快赶紧喝水,慢点吃!我端起茶水,往嘴里直倒,没想到口腔又让热茶烫得不轻,直接吐了出去,父亲反应神速,拍拍我的肩膀。卖茶的老汉这时说道:没事,别着急,已经凉了一会,爷给你免费再送一杯……

西兰公路,西北高,东南低,下坡路多路长,相对轻松。父亲说:现在骑了一半路程,累了多歇一会。我回答:没事,还行。
说实话,我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长的路线,加之正值年少,力气还未饱满,“还行”,也是我对父亲的信心。所以,从父亲高兴的神情上,已经挂满着他对我的满意。
就这样,我和父亲一路向东,相互提醒,注意安全。下陡坡,过咸阳,骑了半天,我一路问了父亲不下十次“到咧么、到西安咧么”。

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来了】
终于到了!我和父亲终于到西安了!伟大的古城,伟大的西安!我这个井底之蛙,我这个农村黑娃,我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——来了。
我自从母亲肚子里出来,只见过印在书本上的高楼、商店和汽车,我哪里见过这么多一座座,一排排,连成一片片,垒成一块块,且威猛宽大的楼房?我哪里见过象潮水一样,一望无际的骑着自行车下班的人流?我哪里一次性见过这么多比农村人穿得好看、长得好看的城市人?
我跟在父亲的车子后面,我们严格遵照城市交通法规行路。父亲骑到哪里,我跟随在哪里,红灯亮了,父亲停下,我立即停下。无论拐多少弯,骑行多少条街道,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乡下娃来说,面对这么多扑面而来的“城市风景”冲击波,我象梦游浩瀚无边的仙境一样,那么兴奋,那么新鲜,那么惊喜——这就是身临其境的大古城,八十年代的大西安。
记得我和父亲赶到西安南门附近时,已到当天中午时分,父亲说:明天才开始正式报名,我们再去小寨西安音乐学院,今天先安排住下和吃饭。
八十年代初期,西安南门外附近的一些建筑,印象比较老旧,没有钟楼沿街繁华。我和父亲在南门附近转了一圈,最后,父亲决定在南门外一家叫“前进旅社”的旅店住了下来。办理完住店手续后,我们开始吃饭,以自带锅盔为主。
吃完饭后,父亲问我:想回到旅店,还是再到街上看看?其实,我当时想到街上继续看看新鲜,长长见识,我一个农村土鳖娃来一趟大省城,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,一想到明天报名,接下来还要考试,想逛街的心情顿然消失了。

【疾风暴雨住夜店】
回到旅馆后,我开始整理东西,拿出铅笔和纸张,准备画画。父亲坐在我的身旁观摩,他以看为主,即是我哪一根线条没有画好或者不够准确,他也不轻易指导或批评。无论在老家或者在当下,这样宽松的环境,是我年少时期最大幸福。
我和父亲住旅馆大房,印象中有十几张床位。那时学画的孩子比较少,是稀罕的缘故,有几个同店的住客发现我在画画,他们围观过来看个热闹。这时,我有些紧张,可能源于没有见过大世面,没有见过宽大笔直的马路,高大的楼房,更没有见过那么多花花绿绿的漂亮的裙子,或者自己本来比较害羞和胆小……我拿笔的手没有方才灵便,我尽量集中精力,目不斜视,尽量控制好心态,后来,画得比较顺畅,效果也好了许多。旁边有人夸奖道:这娃娃画得真好!这娃把这人画得象的太!等等。
下午在旅馆,一口气画到天黑,画了十几张速写和素描,握笔的手已经感觉明显麻木。诚然,和紧握几个小时的自行车手把有直接关系。
父亲,这时从信封里倒出一些茶叶,放进随带的茶缸里,喝了一口茶说:别人对你的夸奖,是对你的鼓励,千万不要骄傲,天外有天,人上有人,不要放在心上,不要沾沾自喜……我知道,这是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,也是“知子莫过于父”的父亲,催我继续努力学习,提高画技的一种支持和期待。
但我,也自知我的绘画实力,也不差。那时在老家学校,因为有此特长,我在学校是老师喜欢的学生,写标语、办黑板报,大多由我包揽。所以,父亲的教诲我当然领教这种提示和关爱,但我心底似乎有声音在说——请父亲放心,你儿子有这个自信,你儿子也是你说那个天外之天!
入夜,父亲陪我忙活了一天,骑了近一百公里的路程,我们爷俩都该歇息了。我和父亲同睡一张床,花了一块五毛钱。我躺在父亲的脚下,一时半会睡不着觉,我想,父亲也不一定睡着。旅馆内已经住满客人,左床客人的呼噜声已经响起,接着,右床客人也开始低节奏地吹起了发声的泡泡。
窗外的夜风,将旅店的窗帘刮了起来,也隐约传来远雷滚动的声音和闪电。那雷声越来越近,几分钟后,直接一个霹雳,砸了下来,仿佛要把旅馆震塌。这时,所有的鼾声已经失踪,有人裹着被单坐在床上。我和父亲也被这雷声震得睡意全无。我对父亲说:西安的雷声都比咱老家的大!父亲没有立即回答,而后淡然地说:这娃,真没见过啥!
这时,窗外又掀起了一阵电闪雷鸣,麻痹的象无数个青面夜叉和天神在打架一样——暴雨,顷刻间轰鸣着,瓢泼而至……
临近窗户旁边有梧桐老树的叶子,瞬间被疾风暴雨撕扯得不想个样子。豆大的雨滴从东窗砸进来的,也有从西窗砸进来的,有人麻利,赶紧关闭好窗户。
突然,电停了,大家一声小呼,接着有人骂道:哎呀,这黑灯瞎火的,又吵蚊子又多,睡也睡不着!此人正在抱怨,楼下传来旅店老板的拖腔高叫声:紧—急—避—雷,临—时—停—电……
父亲坐在床头,我坐在他的旁边,父亲说:没事,夏天这种雷雨来的快,走得也快,现在被刚才小多了!
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功夫,夜叉们鸣金收兵,天神们修改计划等下次再战。夜雨逐渐消停,只听到零星的雨滴声。电来了,旅馆发黄的电灯泡也亮了。父亲看了看手表说:十二点多,还好,能睡上几个小时。
窗外已经彻底恢复了平静。旅馆内,已经有人熄灯,大伙又开始接着睡觉,我的周围有再大的鼾声,我也了若无事,怂管它,安然酣睡——我,困死了!
【西安白跑了一趟】
暴雨过后,午夜凉爽。一夜睡得非常踏实,被蚊虫叮咬也没有受任何影响。父亲早已起床,他叫醒了我,我们洗漱和吃完早饭后,去小寨西安音乐学院报名。
此时,已到上午九点,音乐学院报名处周围,已挤满了前来报考的孩子和许多陪同的家长。父亲帮我排队,我站在他的身旁。不大功夫,轮到我和父亲报名。父亲向接待老师咨询着什么,由于人多吵杂,他们的对话,我一句都没有听清。而后,父亲给老师递了二分硬币,老师递给父亲一份纸张。
我和父亲站在窗口一边,一起阅读这份叫做“西安美术学院附中招生简章”的东西。父亲看着招生简章,却皱起了眉头,脸色也严肃起来。我问父亲怎么了?咋回事?他说:这一趟西安白跑了!人家有要求,必须是初中升高中的应届生,你还小,达不到人家的报名条件,所以,白跑了一趟西安!父亲说罢,我问他:那咱们咋办?他回答:刚才和老师协商,说我们路远,来一趟西安不容易,让娃先报上名吧,老师说,不够条件,说啥都没用。

【跑了一趟省城,办了二分钱的正经事】
父亲说:咱们坐在那个树下,喝口水,咬几口馍,休息一会儿,打道回府!
回家的路上,我和父亲继续穿越省城,由城市南方向,向西北方向原路返回。宽大的高楼林立街道两边,由于正午时分,城市工人们下班的车流和昨天没有什么区别,依然如故,一眼看不到尽头。
街道两边粗壮的法桐的枝叶,罩得树下一路阴凉。路上的行人和汽车时来时往,父亲提高嗓音说:娃,没有啥,权当锻炼身体,了解一下人家的招生情况,你也见个世面,逛了一趟省城。我看父亲甚是高兴,我随他的高兴,心情也不差。
我们沿西兰公路312国道返回。骑行不到三个小时后,又途径昨天卖茶老汉的摊子那里。我和父亲下车后,继续歇息喝茶吃锅盔。父亲鼓励我说:咱们多歇一会儿,下来骑慢些,赶天黑到家就成。父亲理解我,我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长的路程,而且坐在卖茶老汉的硬板凳上,屁股被车座已磨得开始发疼。
休息不到半个小时,我们继续骑车上路。过了礼泉县城以后,继续骑行四十分钟,即可到家。

夕阳西下时分,我和父亲已到家门。母亲迎接我们时说:我在门口向公路上看了三阵子,还不见你们爷俩回来!而后,母亲给我和父亲已经打好洗脸水,洗脸水明显比平时打得更满。
父亲洗完脸,落座后,长舒了一口气,对母亲说:这次到西安,白跑了一趟,办了二分钱的正经事!母亲听罢,面色诧异,她手里端着做好的饭菜,似乎停顿了一下。我怕她着急,我赶紧给母亲一五一十地讲清了我们父子进省城的所有经历和原由。
母亲听罢说:儿呀,我娃受累了。继续好好学习,明年再去西安,你们爷子俩个现在——先吃饭!
那一年,我十四岁。
怀念老屋
文图/石丰
每一个热爱故乡的人,无论他距离家乡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,都会有一种道不完的眷顾和依恋,而组成这些让人一生难以忘怀的情愫或记忆的碎片,无疑便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可磨灭的可以触摸到的----老屋。有人说,老屋是一坛陈年的酒,时间越是久远才能品尝到它的香醇;我想,老屋是一颗划过夜空的彗星,闪闪光华在呵护我们的追问和脚步;老屋,是一首唱不完的歌,风里雨里的凄冷我们总会感知到它的温度。

老屋,也是一出演不完的剧,每一个角落似曾散发出豪迈悠扬的秦腔秦味;老屋,对于久违远离的游子来说,犹如一本历经风残的古书,慢慢被记忆的手指翻动,去寻找最为感动心扉的往事。
我常被故乡的情愫萦绕着,也常被老屋的情结所牵伴着。近几年,每当过年回家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就会远远地发现邻里邻外新建的房子矗立在灰绿色的田野上,显得抢眼,显得亮堂;即便是夕阳西下,暮色降临之际,这些具有秦汉遗风的青瓦大房的新屋,也衬托出肃穆的村庄一派鲜活的气氛。

看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老家经济的逐渐发展,而拆老屋、盖新房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旧去新来,残年老屋会自然越来越少。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老家一部分有胆识、有魄力,会赚钱的乡亲们凭着脑子灵活且吃苦耐劳,想尽办法,使出浑身的解数为幸福生活也整出了名堂。

今年开春以后,在父母和兄嫂的精心操持下,经历三十多年的老屋终于寿终正寝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拔地而起的两层新居。早在多年前,家里就做着建新房的打算,特别是兄嫂从积极筹备到购买各种建材,直至新居完工建成,期间所付出了巨大的辛苦,也实现了父母的一个心愿。
五一放假期间,正值油菜角儿成熟和小麦扬花的时节,我从杭州回了趟老家。此时,老家的房子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中,领队的工匠是我邻村上初中时的同学,由他带领一帮弟兄们打点此事。望着新砌的砖墙和插入墙缝的脚手架,我爬上偿未完工的二楼,努力寻找经历风雨的老屋的踪迹,这融入了我的童年、少年乃至一生情结的老屋以及我梦想出发的地方,就这样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了吗!

老屋已经拆掉,可记忆与留恋愈加清晰、深沉。残存的碎砖和乱瓦散落于面前,我不知为何却有些莫名的落寞起来——老屋,是普通关中民宅的典型代表,风水,坐北朝南,位居整个村庄的东北角上,与村庄连成一片,也被老乡们称为“东城门”巷。据祖父讲在他小时候,乡亲们为了安全其间,防止土匪和盗贼的侵入,村里筑有宽厚的城墙,村里留有东城门和正南门,两门都有砖木结构的门楼。现在,门楼早已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消声匿迹,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城墙根基和那棵源自朱元障时期的皂角树,昭示着老家悠久的历史。

老屋的庄基,长约35米,宽10米;正房三间位于北端,东、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,在当时将这样的结构我们当地称为“一明两暗”。既意为三间正房的中间房子用做“正堂”,所谓“明”,其余两边各房则称为“暗”。而东、西两边的厢房与门房连接起来,由高大而古朴的院墙将老屋整个围拢得严严实实,这一切的布局样式,就是颇具秦汉建筑特色的关中地区的四合院子。

老屋,是由我的小姑夫带领他的徒弟和村上的乡亲们建造的。小姑夫在当时是我们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泥瓦匠,远近由他亲自建造了数十栋房子,在七十年代的农村有这样的手艺是很吃香的事情,尤其是他设计的木梁结构等盖房的诀窍,由于眼力精准,用材得当和经验老道,时常让他的徒弟们望尘莫及。特别是老屋的砖制门楼,由他亲手刻制的青色砖花,错落有致,精妙绝伦,更是小姑夫手艺的集中体现,也是关中民宅建造风格中粗犷有细的见证。

尽管我那时年幼,刚刚能搬动两块砖头,但当年建房的印象我还依然清晰。那时正值七十年代初期,全家共有七口人,祖父、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人;祖父在解放前常年给地主干活,拉了半辈子长工。祖母因病早逝,而父亲通过自己的勤勉努力,在当地乡镇当上了一名店员,后来又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,由最初的每月八元工资,到后来的二三十元,省吃俭用,养活了一家人。时至今日,我也不知道当年父母为建造老屋所需的一切费用付出了多少心血,准备了多少时日。我想,建造这样的房子父母是倾其所有,甚至欠帐也要做的一件大事。

记得当时,我家住在村里的老屋,是祖上留下的遗产。拥挤地居住着户门子三爷、四爷和五爷,共四大家庭。三爷位居老屋的东向,四爷居其中间,五爷居住西边与我家隔壁。在院子中央生长着一棵巨大的香椿树,每到春天就会生发出柔嫩的芽叶,那满院飘香的气息,直钻入人的心扉。叔父们就手握竹竿采摘新鲜的香椿,而后,分给每户一把。母亲就给祖父做一盘香椿炒鸡蛋,这样的美食,在当时只有乡上委派的驻队干部,才能吃到的比较奢侈的下酒菜。

而祖父那时的庄基,仅有一丈三尺宽,全家老小共有两间半的房子,其中一间房屋建好后不久便出现裂缝,遇到雨天,下面就接有瓦盆,叮叮咚咚,不大时辰,雨水溢满。屋里,除了接雨的瓦盆还要防止房屋倒塌,中间用一根木柱支撑,木柱旁边放有大水缸,我常围着柱子和水缸与二哥玩耍和打闹。就这样,几口人挤在一间所谓遮风避雨且锅头连灶的破房子,度过春夏和秋冬。而此时的老屋像一位饱经风霜,病入膏肓的老人,正在难以承受悲喜的负荷和风雨的侵蚀。

我想,对于11岁就到我家当童养媳的母亲来说,足足在这样的屋子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多年,为了支持父亲在外安心工作,为了家庭的生存和希望,也不知母亲熬亮了多少夜晚,拉了多少鞋底,纺了多少穗子缝缝补补,修修糊糊,艰辛地打点着时常没有炊烟的日子和我们混沌的童年。

在老家,建造房子时怕雨天打搅,一般都会选择开春以后,雨水相对少些。现在也是按照这样的节气安排建房的。而那时,父母决定了动工的日期后,便起早贪黑,与盖房的工匠和乡亲们就开始忙碌起来。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母亲来说,除了操持一些盖房的琐碎事情外,主要负责大家的吃饭和伙食,她往往半夜起来就要和面、发面、擀面、切菜、蒸馒头或者烧稀饭等;尽管一整天下来非常疲惫,但她却不知劳累,只知道一鼓作气地憋足劲儿将老屋建成,让全家尽快脱离祖父的危房,住上比较宽松的好房子。
所以,父母通过多年的节俭和努力,在亲戚和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下,终于将新屋建成,先后与新建的邻居连成一片,在当时成为我们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,令邻村许多不认识的路人也发出赞叹的声音。听母亲讲,那时村上有谁家建房,如果在村上人缘很好,只要你招呼一声,就会有许多帮忙的乡亲们前来助阵,是不收取任何工费的。只要给大伙改善一下伙食,吃到可口的饭菜,也就是不错的答谢与回报了。

而对于现在的老屋来说,留下我太多的记忆:春天,有跳跃的麻雀在院中唧唧喳喳,有打闹的老鼠在墙头旁若无人,有雨燕在房檐下衔着泥巴筑槽,有邻居来我家打水,也有老木门的咿呀声划破春天的晨曦,有母亲刚刚烙熟出锅的韭菜合子,也有至今让人直流口水的豆腐菠菜包子。
夏天,有水样的清晨和渗透着花香的黄昏,有牵牛花迎着朝阳怒放,有指甲花吐出鲜红的娇艳,也有蝴蝶跳起轻盈的舞蹈;有萤火虫点亮夏夜,有蟋蟀们正在欢鸣;有雷雨敲打着午后的庭院,也传来祖父轻磨镰刀的声音。 秋天,有火红的辣椒挂满椽头,有金黄色的玉米塔挺立院子中央,有炊烟在老屋袅袅升起,有包谷榛香飘四溢,有晶莹剔透的葡萄,也有架下悠闲寻食的小鸡,有打着鼾声在草蒲上熟睡的懒猫,有小猪在讨着食吃,也有正在要饭的老廉。

冬天,有鸡鸣回荡在静谧的村庄,有上学的伙伴在敲着门栓,有祖父的烟袋和烧得烫手的土炕,有冰凌挂满瓦楞,有落雪铺满墙头。 四季,有童年的玩伴,有年少的淘气,也有我亲手绘制的窗花,有一百单八将在我的画笔下舞刀弄枪,有新春过年时锣鼓敲打在老屋的门前,也有“五好家庭”的牌子欢送进我家;有母亲额前散落的头发和陈年的歌谣,有父亲的教诲和忙碌的背影,有兄嫂的吩咐和支持,也有每次回家母亲送我出门时那依依不舍地情景……
现在,由于我常年在外奔波,老屋少有长住,这朴实无华、历尽沧桑的老屋,融入我太多的情结,也象离别我们二十多年的勤劳宽厚的祖父一样,永远让我怀念。曾经的老屋,终将要离我远去,注定伴我一生幽梦,也带走我所有繁华与零落的记忆,与消逝的老屋作别,岂能没有一丝伤感之意!
一弯冷月,悬挂苍穹,一阵蕴含泥土湿润的清风,演绎出一片浓浓的乡情,也酝酿出朝天呼号的秦声,在我心中久久回荡;又犹如母亲敲打木鱼在默默为儿孙们祈祷,更像是父亲喝过的浓浓酽酽的老茶,在我心中弥漫开来。今夜,寂静无声,花落无痕,暗香飘散;任思绪在键盘上流淌,任往事在心中飞翔。我手捧着为老屋近年所拍的一大批照片,将封存已久的记忆开启,将老屋所有的影象收藏,也将祖上的故事与文化植入我们的根基传承给后代。

我想听你独语,听老屋独语,我想插上夜的翅膀,再回到祖辈那曾经徙身的地方,老屋,是我生根发芽的地方;老屋,也是承载我最初梦想的地方;老屋,不但是我灵魂回归的精神寄托,更是我起步人生和遮风避雨的家园。
网站首页 | 平台介绍 | 联系方式 | 使用协议 | 版权隐私
电话:13996019346
邮箱:393930411@qq.com
Copyring © 2020 中国艺术 渝ICP备20005177号 网站建设:中企动力 重庆